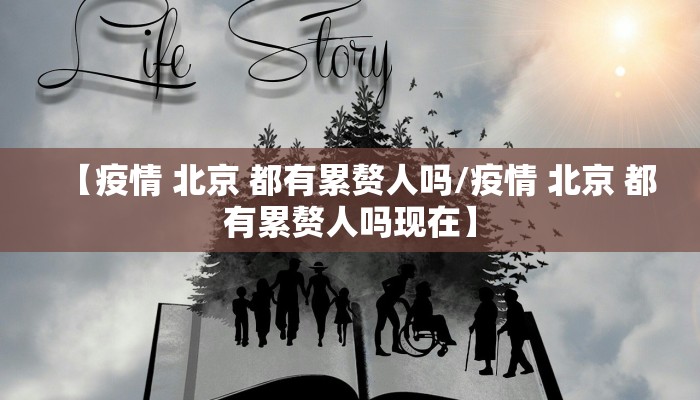
2022年春天的北京,疫情再次袭来,空荡荡的地铁车厢,临时封闭的小区,排着长队的核酸检测点——这座城市仿佛又一次被按下了暂停键,然而在这静默之下,一个尖锐的问题悄然浮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着所谓的“累赘人”?那些无法跟上防疫节奏的群体,是否正在被隐形地边缘化?
“累赘”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标签,在疫情管控的特定语境下,它指向那些因各种原因难以完全符合防疫要求的群体:没有智能手机无法扫码的老人、居住在狭小空间内的务工人员、需要定期去医院的重病患者、还有那些心理健康已然亮起红灯的普通市民,当防疫变成一场需要高度配合的统一行动,那些无法“完美”配合的人,是否不知不觉中被视为了社会的“累赘”?
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其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防疫难度的极端性,朝阳区的白领可以居家办公,快递外卖无缝衔接;但大兴区建筑工地的工人一旦被封控,可能就面临失去日薪收入的困境;东城胡同里的老人或许不会使用健康宝,需要志愿者一次次协助;燕郊通勤族则要面对跨省防疫政策不一致带来的种种难题,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原本就存在的社会不平等暴露得更加明显。
老王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这种困境,作为一位68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疫情几乎切断了他的全部生计。“我不会用智能手机,刚开始那会儿,乘客上车要扫码,我弄不了,只能一天天闲着。”老王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北京市老龄协会数据,全市约有60万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问题,当防疫措施高度依赖数字技术时,这些老人仿佛成了“多余的人”。
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小张和五个同伴合租在回龙观的一间三居室里,当小区因出现阳性病例被封控时,他们不得不全部隔离在狭小的空间内。“工作人员说‘居家隔离’,但对我們来说,这个‘家’连正常活动都困难。”空间上的拥挤只是表面问题,更深层的是他们随时可能失去工作的不安全感——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隔离意味着零收入。
更不为人注意的是那些需要定期就医的特殊群体,李女士每周需要三次肾透析,当小区突然被封时,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我知道防疫重要,但我的身体等不了。”经过多方协调,她最终得以特殊通行,但过程中的焦虑和恐惧难以言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成了社会的负担,就像是个麻烦制造者。”
疫情第三年,心理上的“累赘感”正在无声蔓延,心理咨询热线的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北京市民关于焦虑、抑郁的咨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许多人表面上适应着防疫生活,内心却充满了无力感和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不够坚强?”、“为什么别人都能适应而我却如此痛苦?”这种情绪上的挣扎同样需要被看见和理解。
面对这些现实,北京正在努力寻找平衡点,社区志愿者为老人打印纸质版健康码,街道办事处为隔离中的务工人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医院为特殊患者开辟绿色通道——这些举措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表明这座城市正在尝试用更加精细化的方式应对疫情带来的复杂挑战。
疫情终将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停止: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最容易配合的人,而在于它如何包容那些最难跟上步伐的人,真正先进的防疫体系不是机器般的高效运转,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能够为每个个体保留尊严和空间的艺术。
在北京这座有着两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里,没有人应该是“累赘”,疫情的考验不仅是检测我们的防疫能力,更是检验我们的城市文明程度和人性的温度,当我们能够坦然接纳每个人的不同处境和需求时,我们才能真正说——我们战胜的不仅是病毒,还有我们内心的偏见与冷漠。
发表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来抢沙发吧~